湯舒雯專欄:特區
我在離開美國前去了一趟華盛頓特區。

我在離開美國前去了一趟華盛頓特區。六年來不曾到訪的留學國首都,就像始終沒有見面的筆友,很難說見了面會感覺更熟悉還是更陌生。更準確地說,每個國家的首都大概都像是一部文學經典。正如卡爾維諾在他那經典的《為什麼讀經典》中,對於「經典」的其中一個定義:「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白宮、國會山莊、華盛頓紀念碑⋯⋯更別說那尊林肯巨人了。華府,就好比倫敦、巴黎,甚或它的手足紐約,都是擁有遺產如同擁有天賦的城市。所有那些「帶著先前解釋的特殊氣氛走向我們,背後拖著他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只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跡」(註1),會讓人未曾造訪,就對這座城市生出懷念之情。然而,後來我很快察覺,相對於那些彷彿馱負著古老的行李終於抵達眼前的建築,被我深深低估的,卻是一個最糟糕的時間點。
就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夕,那時疫情和選情同時如火如荼、又相互澆灌有一段時間。壓力在華盛頓特區的街道上蔓延著。幾個月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之死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反警暴示威所造成的洗劫、動亂,仍讓全美商家餘悸猶存。大選倒數一週,首府路上我觸目所及,盡是木然與木色:銀行、飯店、辦公大樓、連鎖超商、咖啡店⋯⋯要不是早已完成工事、門禁森然,要不就只見工人們正忙碌著板上釘釘,在櫥窗和入口處封上大塊大塊的木板。
路上行人寥寥,氣氛蕭索。整個城市彷彿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都在演習和防範,對於一份可能失控的騷動,像在揣摩又像在期待。也是在這一段旅程中,我至今難忘的,是在五次搭乘地鐵的途中,三次受到種族仇視話語的狙擊。
一位街友確保我聽見了中國,聽見了亞洲,和銜接它們之間的含混不清的髒話。另一趟車程中的街友,其咒罵對象包含了台灣和印尼,讓我和旅伴下車後也嘖嘖稱奇。
最後那次,我們才上車坐定就聽見一聲暴喝,隨即,車廂另一頭彈跳起一名醉漢,跨著大步直直朝我們的座位方向走來。他口齒不清地要我們滾出這個國家,一邊在車廂內大力跺步,反覆走去,走回,走去,走回。整個車廂裡其他排的乘客在他經過身邊時都帶著一種文明的矜持,皺著眉,盡量縮小自己,然而只有我們沒有辦法。我們是那個被狙擊槍的瞄準鏡膨脹起來的獵物。那兩站之間的短短數分鐘如此漫長,我直到數個月後才能準確命名它。
那時,距「針對亞裔的仇恨與暴力犯罪」(anti-Asian hate crimes)躍上全美頭條,還早數個月的時間。
真正所謂「最糟糕的時間點」,大概往往是意會到「最糟糕的時間點尚未到來」時。
但是在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傳染病大流行中,後來的這一年裡,我時常想起的,仍是卡爾維諾對於「經典」的各種定義:「大概最理想的辦法,是把『當下』當做我們窗外的噪音來聽,提醒我們外面的交通阻塞和天氣變化,而我們則繼續追隨經典作品的話語,它明白而清晰地迴響在我們的房間裡。」有人的時代裡是羅馬,有人的時代裡是西班牙,還有人會提起某一時期的英國,但在我所生長的這個時代,美國確實是世界裡的「特區」,華盛頓則當然是特區中的特區。那麼像「黑人的命也是命廣場」(Black Lives Matter Plaza),或是我曾置身的那個逼仄的鐵車廂,大概就是類似「特區中的特區中的特區」的存在吧;在列車窗外不可或缺的噪音聲中,一代又一代的留學生,不時會從中帶走一本即使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
註1:卡爾維諾對於「經典」的另一定義。
|延伸閱讀|
購買 VERSE 雜誌
 本文轉載自《VERSE》009
本文轉載自《VERSE》009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致力於挖掘台灣文化,請支持我們正在進行的第三年訂閱計畫,一起記錄與參與台灣的文化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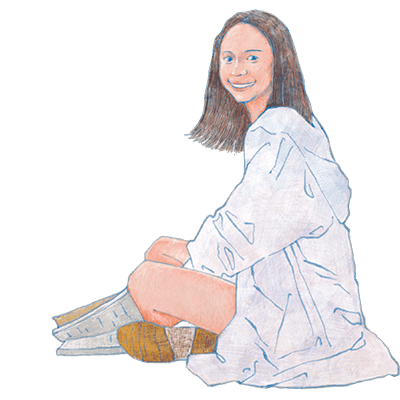
湯舒雯
台大政治系學士,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目前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亞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作品曾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靈魂的領地:國民散文讀本》、《台灣七年級散文金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