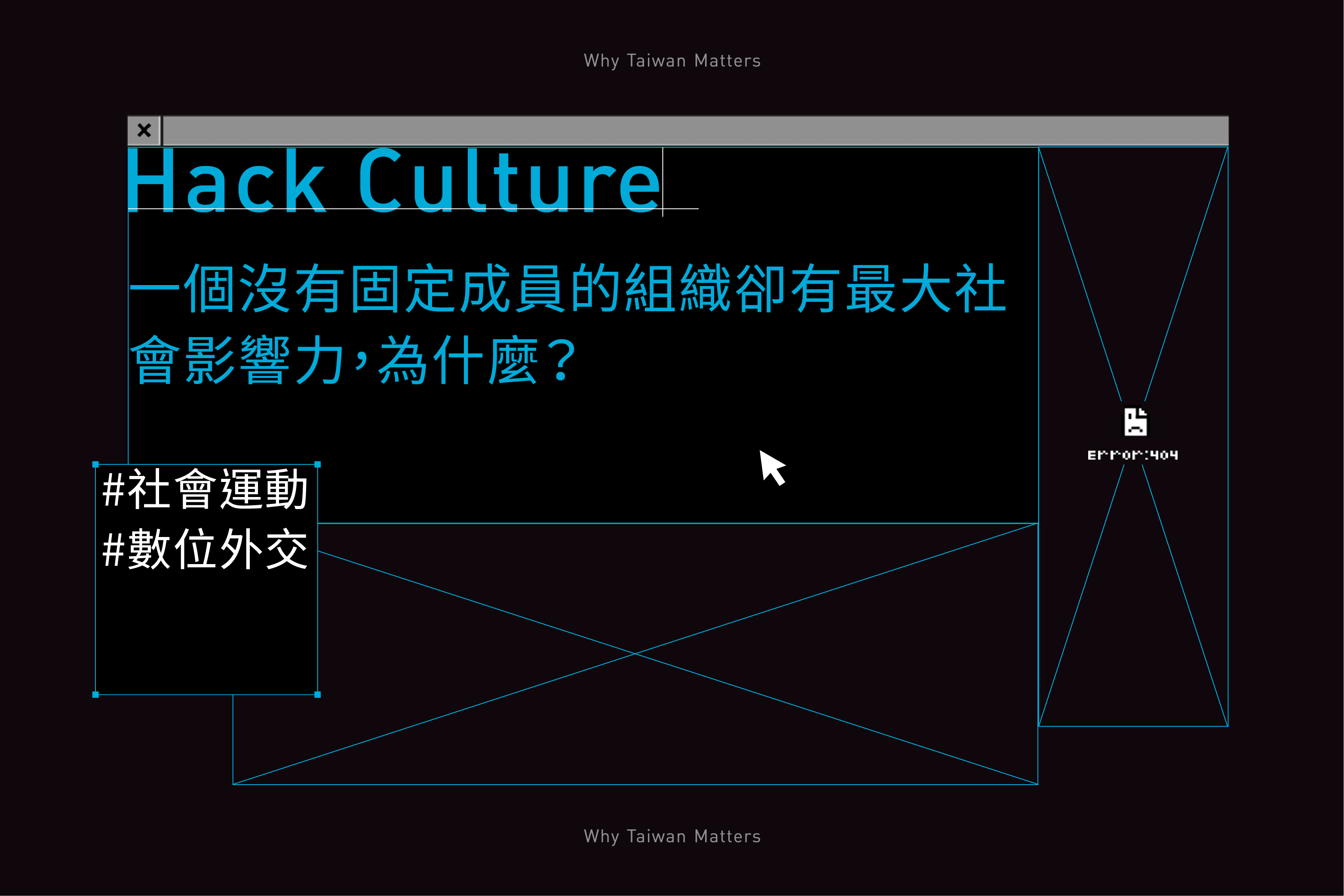台灣公民科技如何活躍於世界?
一個沒有固定成員的組織卻有最大社會影響力,為什麼?
「沒有人就是任何人」的特性,反而包含了每個人的參與性,這股以科技驅動公民運動的力量如強風吹拂,從台灣到國際,挑戰不合理,創造新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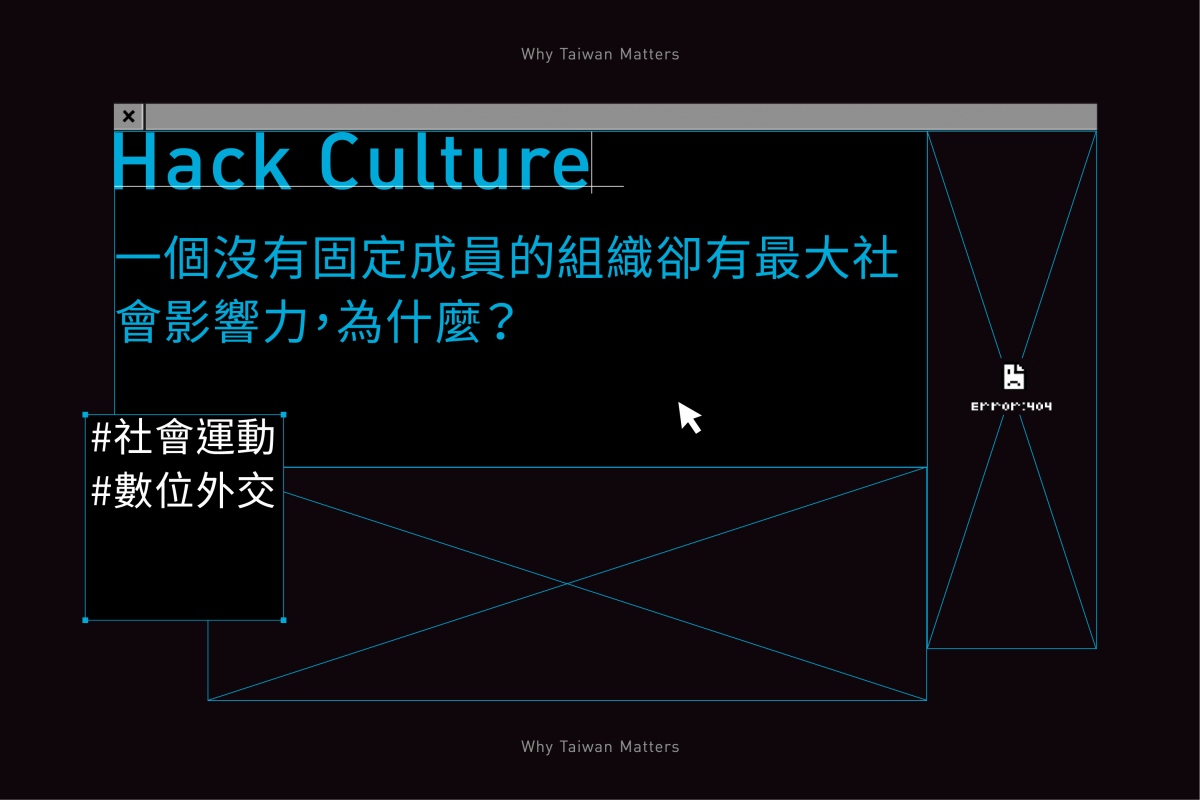
「沒有人就是任何人」的特性,反而包含了每個人的參與性,這股以科技驅動公民運動的力量如強風吹拂,從台灣到國際,挑戰不合理,創造新的可能。
從社運長出的科技發展
近年,科技開始大量出現在台灣的社運場合,幾乎讓老舊過熱的政府機器無所適從。
2008 年的野草莓直播,可以說是台灣公民科技的一個起點,自此,2014 年以後太陽花運動的社群串連、現場直播、WiMAX、反訊號遮蔽等等,儼然是現代公民科技的火力集中展示。同年十月,香港年輕一代共享了台灣的運動經驗,以 FireChat 分散式熱點技術,跳過國家基礎建設,在沒有網路的情形下傳遞訊息,直接與港警的監聽進行攻防。
去年底,加泰隆尼亞的「民主海嘯」,亦有超過 36 萬名使用者利用開源通訊軟體 Telegram 加入示威串聯、甚至有運動者自行開發 Android App 供下載,可說是一場真正「科技驅動」的公民運動。
「只要有足夠的眼睛,就能讓所有問題浮現。」這句以開放系統 Linux 發明人林奈斯命名的定律(Linus’s law),彷彿就是公民科技的證言。在每個當下,以一把把隱形的科技之傘,經由公民手中顯現莫之能禦的物理性,挺身抵抗時代黑雨。
2012 年台灣的一群工程師,因為不滿政府「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廣告,舉辦「第零次動員戡亂黑客松」,訴求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並「成立」了零時政府 g0v。然而,正如 g0v 參與者 pm5 指出的:「g0v 不是一個組織,沒有發言人、沒有固定組織架構」(註 1),人員可以隨時來去,更像是近年港台社會運動無大台、去中心的參與模式。
沒有人代表 g0v,但「沒有人」就是你,沒有人就是任何人。g0v 的「組成」,非常類似紛雜多元、卻具有強大參與動能的台灣社會,能以輕小、靈活的游擊方式組成不同專案小組,嘗試出不同的議題解決方案。從最草根的關注(如阿美族語辭典)到普世關懷(如台灣輻射地圖),再到引起各國關注的「口罩地圖」,都是 g0v 社群專案協作的具體成果。
而除了每兩個月定期激盪專案的黑客松,g0v 雙年會「零時政府高峰會」(g0v Summit)每次都有不少國際駭客參加,2018 年更吸引超過 23 國講者現場參與,包括巴西、德國、印度,甚至言論空間被高度限制的中國網路運動者、西藏流亡政府資安人員等,分享各國公民科技發展的困境與突圍,讓「零時政府高峰會」成為亞洲最大的公民科技年會。
事實上,台灣的公民科技社群也正朝「機構化」的方向邁進。2014 年由 g0v「村長」高嘉良、開源人年會 COSCUP、OSDC 等開源社群共同發起,向台北市政府申請成立的「開放文化基金會」(Open Culture Foundation),近年來更資助不同民間參與者出國交流,進一步將公民科技、網路治理與開放政府的在地實踐經驗,系統化地推向世界。
資源不多,更要「一起玩」
然而,大國的文化輸出卻也經常壓縮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長期將台灣數位經驗帶向國際,協助與台灣處境類似的科索沃爭取「網域名」的數位外交協會理事長郭家佑比喻:「像中國的『孔子學院』有資源,可以大灑幣,但他們做這些事的前提,是認定外國人很仰慕中國文化。」
反觀台灣,沒有大國雄厚資本,卻有許多「一起玩」的網路游擊經驗,無論藍、綠支持者,都已對線上遊說、社群動員非常熟悉。「我就去搜尋、串連科索沃的粉絲專頁,把科索沃人、台灣人加入同個社群,有了兩邊的網路聲量,就能夠做一些事,比如一起辦展,」郭家佑說,「這其實是一種朋友間的價值交換,一種社會攪動,而且這樣也比較省錢。」她笑說。
在年輕行動者的眼中,「好玩」和友誼,甚至可能突破國際政治的硬現實,擴散影響到同溫層之外。科索沃一家獨立媒體《Kosovo 2.0》的主編,在採訪完郭家佑後,曾私下跟她透露:「其實我們不大能寫出『台灣』兩字,因為有拿歐盟補助。但現在管它的,我就是要寫。」她說,「這就是人家真的把你當好朋友的表現。」
「重要的是,」郭家佑感性地說,「科索沃人五年後回來看,會記得有台灣人和他們一起努力過。」
台灣與世界,迎來公民科技的逆風期
只是網路科技並非僅是讓公民權起飛的「單向吹拂之風」。根據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調查,全球網路自由度已連續九年退步,中國、伊朗依然名列最末,即使美國也連三年倒退。掌握大數據的跨國企業、駭客傭兵組織、集權政體與極端民族主義者,正形成一股巨大的暗流,吞噬網路世界自由開放的核心價值。
例如曾被 Netflix 拍成紀錄片的英國「劍橋分析」公司,就藉由非法取得的大量用戶數據、使用習慣、結合演算法與社群流行塑造手法,鼓動非裔年輕人以「疏離政治議題」為時尚,造成千里達及多巴哥的印度黨勝選。
而當生活中不能沒有科技,人們卻喪失對科技的主導權時,有時就只能選擇更激進的「虛擬流亡」(Virtual Exile)做抗議,如中國網路行動者發起的「逃離微信」運動,參與者付出了喪失既有社會扭帶、生活機能(包括搭車、電子支付、乃至上下班打卡)停擺的巨大代價,只為了能在「牆外」更自由地思考與言說。
台灣也不能自外於這一波衝擊。深入研究網路政治、輿論操作的逢甲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王銘宏指出,在不遠的未來,運用深度偽造(Deepfake) 技術來生成名人演說假影像的「認知攻擊」、及類似數位身分識別證的「個資集中化」帶來的資安風險,都可能成為台灣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隱憂。
以行動主義,重建生活的真實性
但歸根結柢,公民科技必須直面的卻是對「公民」兩字的挑戰。根據 g0v 的 MG Lee 紀錄,2018 年參與台灣 g0v 峰會的印度裔女性講者安娜蘇亞塞吉普塔 (Anasuya Sengupta)曾指出,數位科技經常是「只為強勢的語言和文化」服務,排除更多元族群的參與機會,進而質問使用科技主體的「我們」到底是誰。王銘宏教授也強調,良好的公民科技應該對「低度科技使用者」(如身障者、高齡者、外配)提供參與和利用的可能性。
這不只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而是將「科技」本身放在公民權利角度下思考的必然結果。例如 g0v 舉辦的黑客松,就提供兒童休憩區,讓有家室者也能持續參與活動,而無論 g0v 活動首頁或黑客松現場,都強調對性別友善守則的具體規範,讓「公民」與「科技」成為兩個無法分開的概念。
實際上,「科技」一詞的希臘詞源 τέχνη-λογία,最初就帶有技藝、巧妙的手工等意含,是以質樸的行動主義,穿透意識形態的幻覺,去徒手打造日常生活的真實性,藉此安身立命。
而「開放與分享」則是連繫這些科技行動者的重要價值;正如台灣開發者從全球的開源程式庫 GitHub 中取得可用的程式模組,加以改寫、解決在地問題,再將成果與專案經驗釋出,讓國外開發者用以解決其他地區的類似情況——在這個意義上,台灣已經重返世界。
或者,在一個更好的社會想像中,台灣與世界將不再有區別。
註1:CC BY 4.0 by《VERSE》 & g0v contributors
回到專題:Why Taiwan 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