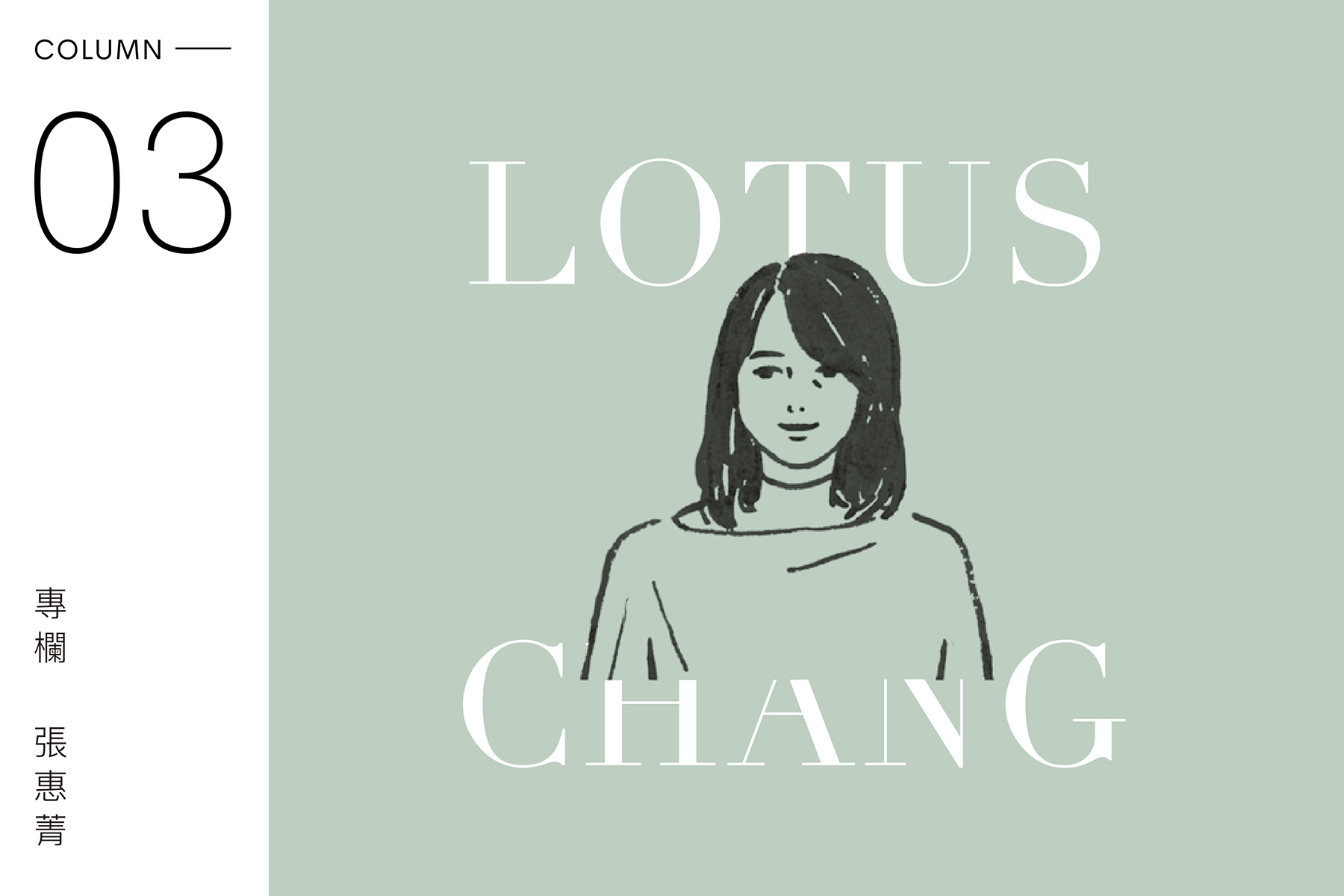張惠菁:第一次說出
張惠菁專欄:重新解讀台灣史 答案無法一眼看盡的旅程
對還在不斷認識自己歷史的我們而言,能從台灣歷史中學到的一課即:歷史不會是一道答案全部已知的問題,不是一趟終點全能看見的旅程。

有時人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某些下意識的制約,變得只問自己知道答案的問題。變得不再真正出於好奇而問。變得期待一切事物都要在兩分鐘之內,用已知字詞被解釋清楚。變得不再看向沒有答案的方位。而在不知不覺間,限制靈魂轉動的力矩。
倒帶回起首的句子,我本來寫的是:有一種人只問自己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有一種人。然後我想了想,我也有可能那樣。那不是一種人的分類:你會,我不會,他會,他們不會;而是一種慣性的結果——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那習慣,如果放任自己被制約的話。
可能是因為早晚匆忙的出門時間,因為工作的時長,因為社交對話所能容許的冷場秒數,或在社群媒體上的反應速度⋯⋯等等,我自己也有可能成了這種人。我提醒自己,你要盡力從一切使你落入那種習慣的拖曳力量中脫身。
其實台灣的歷史、台灣周邊地域的歷史,「我們」是誰的故事,這裡面就充滿了無法用簡短答案回答的問題。近年每當讀台灣史研究,我總是覺得自己很無知(當然這要感謝幾代台灣史學者不斷累積新的成果所致)。一方面為那無知而慚愧,一方面安慰自己還有大片的知識待補可以去了解。大抵就是在這樣一種,又焦慮又好奇的情緒之中,獲得對歷史的新認識。
我往好處想,告訴自己:那是因為所有過去以為已經知道的,現在鬆動了。
包圍著認知的那些牆,磚塊掉落下來,使你看到牆的後面原來還有大片的空間。還想要了解原住民角度的歷史,平埔族的大遷徙。走進台南延平郡王祠會還想要了解留在其中的日本神社祭物,也想了解一下淡水與清法戰爭的關係。
你也是這樣閱讀歷史的嗎?在接受知識的補血的同時,一邊感到還有那麼多的事物你不知其所從來、所演變。一邊讀史料,一邊就會意識到歷史上的無聲者比發聲者更多。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如此。因為歷史的行為主體,當中有無文字傳統的原住民,有無法為自己寫下歷史的人。
歷史小說家錢真說她在寫《羅漢門》(朱一貴事件)的時候,心裡很清楚,史料中留有文字的不可能是故事的全部。因為這些史料的書寫者,比如寫了《平臺記略》的藍鼎元,本身就是大清帝國派來平定朱一貴的軍中幕僚,因此是「平亂者」的視角。朱一貴和他的朋友心中想什麼?為什麼會發動起義?錢真研究了他們的口供。
但即使如此,也仍然要知道,口供是這些人被擒之後,面對官府而說的話,許多人的口供言語是破碎的,未必能還原一切。朱一貴是他們當中將造反理由、對官府哪些舉措不滿說得相對清楚的——他果然是帶頭的領袖。錢真讀遍了這些檔案,知道真實止步在「文字」記述之外(而在那個時代文字本身即是權力)。於是他開始有意識地「虛構」,讓朱一貴和他的朋友們說話。
在這例子中,「虛構」本身有一種真實的意義。也許對像我們這樣,還在不斷認識自己歷史的人而言,能從台灣歷史中學到的一課即是:歷史不會是一道答案全部已知的問題,不是一趟終點全能看見的旅程。
布列松說,拍出好照片的唯一祕訣是「讓自己處於接受狀態」(be receptive)。或許,對我們這樣的人群而言,恆常「處於接受狀態」格外重要——問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即使答案令我們驚愕,好過認為自己已知道一切。因為有許多事我們不知道。許多人群的視角、各種的故事,如底片上的感光等待被顯相,問題等待被問出。
購買 VERSE 雜誌
本文轉載自《VERSE》003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

張惠菁
台大歷史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碩士。1998 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流浪在海綿城市》,其後陸續發表有小說集《惡寒》與《末日早晨》,及《閉上眼睛數到十》、《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步行書》、《雙城通訊》、《比霧更深的地方》等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