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入圍
專訪《修行》導演錢翔:守住婚姻到底得到什麼?
相隔7年,導演錢翔再度與演員陳湘琪合作拍攝電影《修行》,男主角則由陳以文擔綱。本片獲入圍第58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改編劇本獎,也在今年台北電影節入圍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

導演錢翔睽違多年再度推出長篇電影《修行》,改編自王定國短篇小說《妖精》。(攝影/汪正翔)
相隔7年,導演錢翔再度與演員陳湘琪合作拍攝電影《修行》,男主角則由陳以文擔綱。《修行》改編自王定國短篇小說《妖精》,講述一對夫妻到療養院探望罹患失智、老公曾經的外遇對象,故事視角繞在老婆嚴太太身上,看她守著婚姻之名,卻也同時困住自己的窘境。本片獲入圍第58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改編劇本獎,也在今年台北電影節入圍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
「然而當我把車頭調回來,這一瞬間我卻看到了,她忽然停下了腳步,悄悄掩在一處無人的角落,那兩隻眼睛因著想要凝望而變得異常瑩亮,偷偷朝我們的車窗望過來直視過來。」——王定國《妖精》
導演錢翔第一次讀王定國短篇小說《妖精》時,就被妖精一角給打到,特別是故事結尾處,他直言那太精彩了。妖精,是母親說的,指稱那位父親曾經的外遇對象,她因失智住進了療養院。「看起來是失智,但實際上眼睛清晰,靈魂某個地方是開的,像是某種神秘召喚,好迷人。」
當初一讀完,錢翔難掩興奮之情,到處向友人推薦,「這小說精彩,趕快拿去拍。」2017年,這故事被拍成了電視劇《閱讀時光2:妖精》。
但故事裡的母親卻隱隱搔撓著錢翔。作為影像創作者,閱讀小說,腦袋也同時將其影像化,「但日子久了會沈澱,會忘掉細節,唯一留下來的就是母親。」他說,後來已經不太在乎那位妖精與父親,但時刻擔憂著那位母親,「因為她必須承受所有一切,就算她挽回了(這段婚姻),或者她出征,凱旋而歸。她到底得到了什麼?」
卡著心裡,就不得不處理。而當開始轉換故事視角到太太身上,「這個事情開始變得不太一樣了。」錢翔說。

錢翔再度與前作《迴光奏鳴曲》主角陳湘琪合作。(圖片/《修行》提供)
錢翔上一部長片作品是2014年的《迴光奏鳴曲》,同樣是從女性出發,談受困在家庭裡的更年期女性,孩子長大離家、丈夫長年在外地,她過著每日醫院看照婆婆的空虛生活。由陳湘琪飾演女主角玲子,並憑藉該角獲得第16屆台北電影獎與第51屆金馬獎雙料影后頭銜。
碰撞
時隔7年,再與陳湘琪合作推出長片作品,故事改編自短篇小說《妖精》,主角同樣是家庭中的中年女性——嚴太太。不過,對錢翔來說,每一次作品都是全新開始,主角也都是各自長成,玲子並無有意無意地轉嫁到嚴太太的模樣上。「與其談性別,不如來談角色吧。」在我一再追問女性視角時,導演這麼回。
沿襲上一次拍片經驗所學到的,是前置作業的田野調查,「我唯一學會的,就是不要先開口,先詢問團隊裡的女性。」
詢問,是為了得到不同人對待一事的價值碰撞。錢翔不信仰婚姻的幸福美好,演員陳湘琪倒是相反,但兩人反而因此對嚴太太一角的發展充滿興奮。嚴太太的人物塑造過程,是錢翔寫完劇本,拿給製片陳保英、演員陳湘琪看,「陳湘琪會進入角色的心理狀態,去思考(劇本裡)的這件事、這行為,她會不會去做。」
導演以哭戲為例,「像是何時哭泣,我完全不會知道,我不會在劇本上寫『這場哭』,寫不出來這種東西的,只能寫事件,而事件丟到演員身上,經過它們的道德判斷系統,會出來一個什麼東西,那才是我期待的。」
碰撞能招來新的輸入,這是錢翔的方法論。談到透過閱讀汲取創作靈感,錢翔特別強調:「閱讀不光是閱讀,閱讀是一種衝撞,是這些內容對於我的價值觀,有什麼打架的地方,把我的世界撞開了什麼。那東西有意思,可能讓我不安,可能讓我愉悅。但我更喜歡撞到讓我不安的東西。」

《修行》集結了陳湘琪(左)與陳以文(右)兩大影后/帝級演員同台飆戲。(圖片/《修行》提供)
動物性
片名「修行」也來自某次田調經驗的衝擊。田調過程中,錢翔與團隊發現,許多稱不上幸福美滿的婚姻關係裡的人,會找尋婚姻之外的依靠,投入慈濟、教會或醫院義工因此也特別挑選提供心靈寄託的單位進行田調。
電影裡,嚴太太揮舞著手,不斷嘎嘎嘎學著鳥叫,聽從師父把心中委屈憤懣隨叫聲宣洩而出。那一幕完全移植田調現場,「有一天,我們找到這個單位,裡頭有20到30人,老師在前面說著:『把你所有不滿所有積壓都叫說來。』嘎嘎嘎,每一個都在哭,只有一個老先生沒哭,湘琪沒哭,我沒哭。那一幕我很震撼,心想裡頭到底有多少辛苦。我跟陳湘琪對看一眼,就確定是這一個修行狀態,是那一剎那決定的。」
對於婚姻抱持極度懷疑,是年過半百的錢翔看著身邊人的婚姻,各個都出現某種「狀態」,「也不是出問題,而是處在一個懸而未解,落不下地,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不碰最好,是個奇特的狀態。」
電影裡,教養院的鳥困在地下室,飛不上天;嚴家養的狗不知道到哪「亂性」,得了性病。錢翔解釋,鳥與狗並無指涉,他引用陳湘琪曾說:「演員最怕跟動物、小孩眼好,因為他們絕對的真實與誠實。」
這是動物的好處,「演員與他們在一起,就可以看見那其中的差距。」錢翔說,這部電影裡有個前提設定,他相信人有個本性,姑且稱之為動物性,「我們作為人類,本我與超我一直在鬥爭,那個動物性的東西是什麼?那東西主宰我們大量的生活,那麼,本性錯了嗎?應該接受被人為律法的限制嗎?」
那些問句,錢翔自己也還沒有答案,但他期待觀眾看到電影裡的鳥與狗,能夠感受到某種刺激,「對我來說,那個感受反而才是重要的。」

錢翔認為攝影必須倚靠情感去運鏡。(圖片/《修行》提供)
留下思考
「面對一張毫無回應的臉,在母親看來不知是喜是悲,也許本來都想好了,譬如她要宣洩的怨恨,她無端承受的傷痕要趁個機會排解,沒想到對手太弱了。她把手絹收進皮包,哼著鼻音走出了廊外。」——王定國《妖精》
「她認得你。」嚴太太在教養院,當著妖精的面問著嚴先生。錢翔說,有沒有認出來一點都不重要,「(看到妖精後的)後續那些反應都是人給自己的。嚴太太一直被綁在那個裡頭,要不要逃出來,必須留給她自己去思考。」
那些戲裡的引子,也如同錢翔交給劇組團隊的劇本。前製期,錢翔與演員陳以文、陳湘琪來來回回,無數次討論著男女主角的狀態,正式開拍後,現場便不排戲,唯一討論的是「怎麼樣不受傷」,「陳湘琪也常在拍攝現場說,她不知道等下(開演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錢翔笑著形容,拍攝的那一個月,他就是坐在第一排看一流演員演戲的觀眾。
錢翔信仰電影是集體創作,「雖然我身兼這部片的編劇、導演和攝影,讓它看起來像是『作者電影』,但不是的,若是這樣,片子會慘不忍睹,我沒那個能耐。一個人坐在那裡寫的東西,既狹小又偏頗,東西出來會非常難看,單薄。所以我需要有很多意見丟進來。」

在錢翔心中,所有創作背後的議題都是相同的:人的狀態為何?以及面臨到什麼?(攝影/汪正翔)
採訪過程中,錢翔多次直呼「拍片太好玩」,過去,錢翔在商業電影工業裡擔任攝影師逾二十年,如今自己做導演,他選擇回歸獨立製作的現場,拿掉制式流程與規矩,現場就是個大型創作場域。他說,片場時時刻刻都在發生驚喜,前一分鐘美術陳設,後一分鐘演員因應角色再更換擺設,「雖然是我寫的劇本,但(拍攝)當下都有一種很有意思的新鮮感在那。」
錢翔也特別提到拍攝方式,並非事先定好取景位置,而是倚靠著他的情感移動著,「攝影機對我而言是有不同情感的,我太熟悉這個東西,我會跟它互動。比如說我們進到一個房間拍攝,一到房間我會開始找,應該看待這件事發生的位置,等演員演到一段落,再思考我想不想往前進看他。」
下一部作品依舊圍繞著家庭裡的人嗎?錢翔解釋,國家與家庭只差在規模,所談的議題都是一樣的,「所有創作背後的議題都是相同的,我們幹嗎在這裡以這樣子的狀態存在著?而我們以這樣子的狀態存在著,我們到底會面臨到什麼樣子的東西?」
錢翔在電影裡一再拋出問題,那是面對自己心中思索,也是給觀眾的禮物。《修行》最後一幕,嚴太太與嚴先生坐在計程車上,兩人各靠著一方,沒有可以說的,只能望向他方,那一幕長達數秒,「若你在婚姻裡,看到這最後一幕,會給自己下一個結論的:『若我呢?』」
|延伸閱讀|
➤ 訂閱VERSE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
回到專題:誰是最佳導演?2022台北電影節入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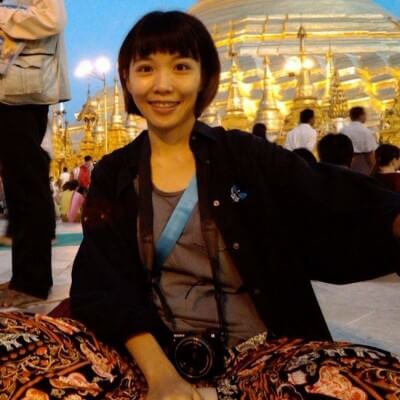
蘇曉凡
文字工作者。畢業於政大新聞所。喜歡故事、認識人和社會,有感於文字的重量。曾任《VERSE》資深編輯、天下雜誌記者、風傳媒編輯、娛樂重擊特約採訪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