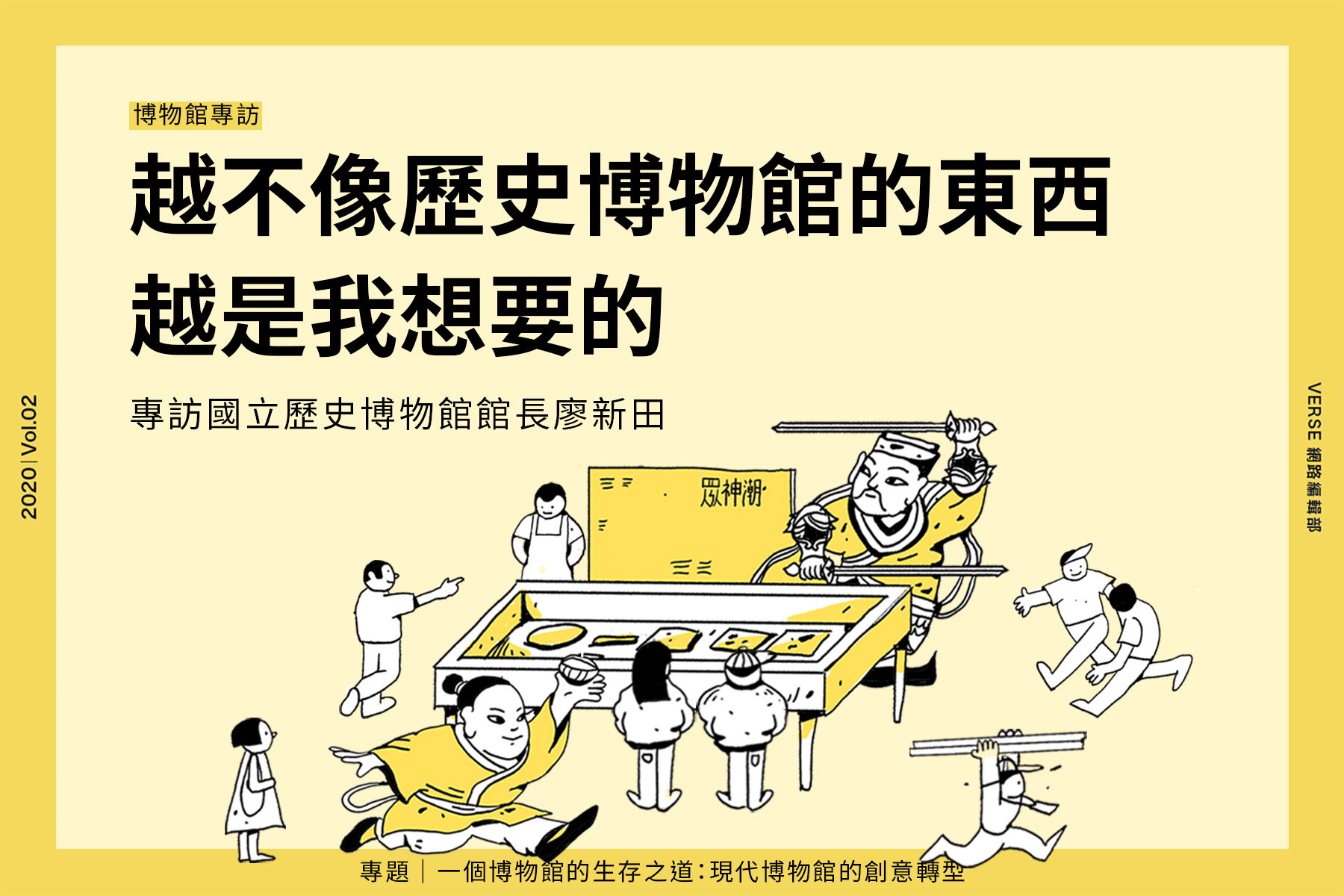專題|一個博物館的生存之道:現代博物館的創意轉型
越不像歷史博物館的東西越是我想要的:專訪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
「先說我後來得出的原則跟結論,就是越不像歷史博物館的東西越好,越是我想要的。」談起這幾年,國立歷史博物館(後稱史博館)縱使修館也休館中,卻反倒開創出更明確的策展動能,館長廖新田絲毫不是玩笑話地切入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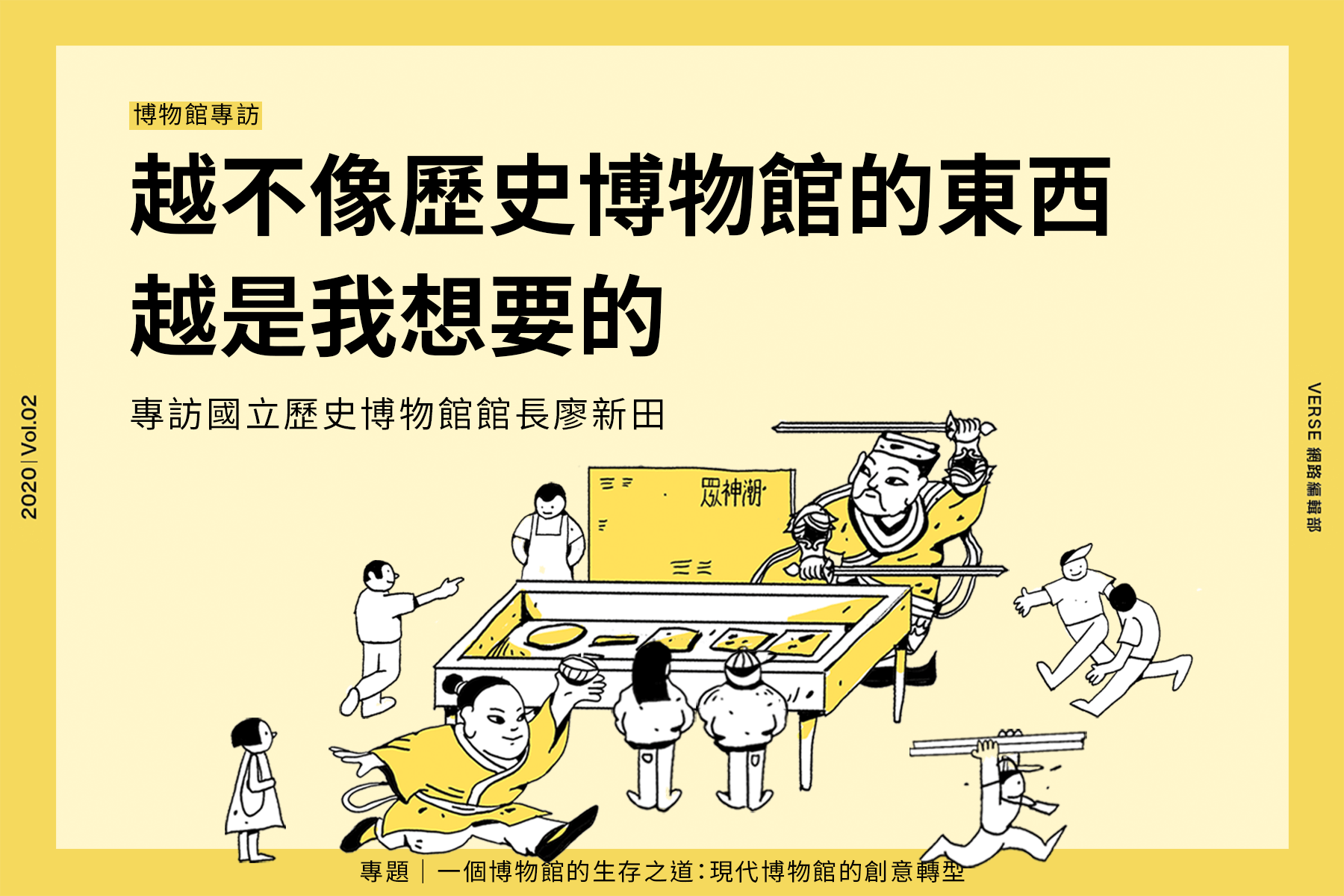
「先說我後來得出的原則跟結論,就是越不像歷史博物館的東西越好,越是我想要的。」談起這幾年,國立歷史博物館(後稱史博館)縱使修館也休館中,卻反倒開創出更明確的策展動能,館長廖新田絲毫不是玩笑話地切入主題。
而在深究它如何轉變之前,總得先了解史博館握有怎樣的背景與條件。1955 年以「歷史文物美術館」為定位,如今邁入耳順之年,史博館作為台灣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始終與戰後台灣文化的發展軸線高度重合,更直球地,我們不妨這麼說吧——六十五年的時間裡,台灣的模樣是什麼,史博館就做什麼。
無所不展的歷史文物館
經歷過十四任館長、一次改名、兩種建築型態,史博館從起初雙層木構的日式建築逐步改建為後來為人熟知的中式宮廷風格;由前身的「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更名為今日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而至於時代更迭之下的館務營運,廖新田則直爽地說,「每一任館長都有階段的使命,但我們一直都是歷史博物館的外殼、國家畫廊和文物館的運作方向。」於是,當 1960 年代,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史博館就做起「中國書畫藝術世界巡展」;而九〇年代中後期,西洋美術在台灣備受討論,時任館長黃光男便與歐洲的美術館合作,帶入不同的西洋美術大展。
但正當你誤以為,多屆美術研究、藝術家背景的館長,搭載戰後台灣美術的路線設定,這座博物館想當然是生人勿近,廖新田又冷不防地表示:「不過回想起來,我們什麼怪裡怪氣的展都辦過。」展皮雕、展音樂、展天鵝娃娃,書展、旅遊展、月球岩石展,「什麼都不奇怪,它就是典型像 eBay 一樣。」又是幽默的神來一筆。

博物館群的先行者
因為身處時代的先鋒位置,很長的時間裡,台灣展覽場館的空乏,都是由史博館一肩扛下,「我們就談幾個時間點:1955 年歷史博物館開幕,1965 年故宮開幕,差十年,這之間沒有任何一個展場,所以有展覽只能到我們這裡。」而接著,雖然迎來了故宮,卻沒有等到清宮本展之外的展量分擔,「所以史博館就繼續展、繼續展,到 1983 年台北市立美館成立,展什麼,展現代美術,一樣不展傳統的東西。」他像是一列穿梭時光的火車,一路盤點台灣美術館的創建史,史博館多重且彈性的歷史定位也逐步清晰。
「在這種博物館的生態之下,它變成了一個獨賣、專賣的生意,完全不是故意,就只是沒有其他人而已。」廖新田準確地提出觀點。聽到這裡,史博館如何達至創新,已然不是太叫人疑惑的課題,在它老早千回百轉、循著社會發展的調適與因應之下,與時俱進是習慣,而變通的柔軟身段則根本是深植的基因。
 正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臨時辦公室接受 VERSE 網路編輯團隊採訪的館長廖新田
正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臨時辦公室接受 VERSE 網路編輯團隊採訪的館長廖新田
當史博館成為時代文化的代名詞
廖新田接著在時空脈絡之下以物件打起比方,他描述,國立歷史博物館就像台灣的窗子、盒子和鏡子。窗子,代表著博物館始終身為台灣戰後三十的文化櫥窗,展演著不同階段的藝文樣貌;而記憶的盒子,指的是一甲子的時間裡,滿滿藝術家的記憶,都珍藏其中,沒有受潮、沒有變調。至於鏡子,是一方台灣歷史的明鏡,反映著文化認同的變遷。
當史博館成了對照時代的文化概念,至此,關於這座靈活卻古老的博物館的靈魂追問,或許(在已經數不清第幾回進化之後)應該更聚焦為——這一次,史博館又會如何與社會對話?
就像你看我,我們都年輕過,只是現在老了。歷史博物館有過它風華的年代,看過人生百態、比以前更內斂,就像老頭子的身體裡充滿了各種歷練,現在最重要的是讓年輕世代看見。
廖新田笑著說。
於是,館刊改版、展覽結合當代設計、展品導入文創操作等,進入修館階段之後,本來就沒有包袱的史博館,變得加倍自由;無牆博物館的想像也在空間卸載的瞬間,再無藉口的突飛猛進起來,「我們突然發現沒有了場館的負擔,有點像置之死地而後生,你必須開始跟不同的設計師合作,必須跟中研院、南美館合作,現在,我們甚至也在立法院、監察院都有展覽。」
除卻了實體,廖新田說,史博館的身段像是從蜘蛛變成蜜蜂,不再守著自己的領地,而是向外採集、轉化能量,「以展覽『眾神潮』的討論過程來說,我的感覺是,我們史博館以前都擺著一張撲克臉,但後來接觸到這些年輕人做的展覽和設計,那個東西很不像歷史博物館,但卻是很好的。」幾次的經驗之下,他發現博物館越堅持定見,就越容易受困、不可能向前邁步;反倒是鬆手之後,陪伴者的角色不僅與外部協作更順利,成果也往往超出預期,所以才有了他老是掛在嘴上、叮囑同仁「越不像越好」的合作原則。

小資轉型的科技逆襲
廖新田深諳史博館唯有帶入新的觀眾,才能永保青春,而文創就是一種招手,當藏品的紋樣成了身上的領帶、古畫中的神像印上了玻璃杯具,文物的翻玩讓博物館有了更遼闊的受眾。加上虛擬實境結合紙本地圖、實體展覽線上化等他所謂的「小資科技」,到頭來,關鍵總是如何建立有效而多元的溝通管道。
只見廖新田一會兒興味十足地拿起地圖,解釋如何透過地點結合展品,最後以 QR Code 呈現,「例如黃土水的雕塑是在龍山寺裡,我們就去拍,然後你掃這邊就能看到影片。」接著,又開心地起身到電腦前,打開史博館線上展覽頁面,點下進入展場、開始環景輪播,「我們早就知道,新的科技趨勢是大家喜歡用線上版,我們做展覽的時候,就會把展場記錄下來,目前線上展大概有十幾檔。」譬如去年與南美館合作展出的〈寶島長春圖〉,全長 66 公尺的圖面,配上現代版的〈望春風〉,別有一番沈浸感。「因為後置,就可以加入更多東西!」廖新田帶著一絲絲驕傲地說。
當然,史博館的活力充沛不止於此,除了常態性的「史博藝術家日」、「世界華人藝術家百年身影」等企劃;12月即將到來的館慶,更會推出史無前例的《台灣美術史辭典1.0》以及第一本「巴西聖保羅雙年展」彙編。
「台灣一直都有在談中國藝術史、西洋藝術史,卻沒有台灣史。這本辭典我們花了大概三年的時間,選出兩百個詞條、每條三百到七百字不等,這是重建戰後台灣美術史的重要步伐。」廖新田仔細地解說著,卻完全可以想見,對於他與他身後的一群台灣美術史研究學者來說,一本真正屬於台灣的美術辭典如何緊要,而這也是國立歷史博物館在向外拓展業務之餘,不望初心的扎根。
 透過小資數位科技轉型,讓民眾可以透過更多媒介「踏入博物館」。
透過小資數位科技轉型,讓民眾可以透過更多媒介「踏入博物館」。
現在是過去的未來
他說,博物館之必要,是讓人認識到自身存在的意義,以及與身處土地的連結,若是你不好奇自己的文化、人為什麼活著,那便可以選擇不踏進館裡。然而,「作為一個館長,我需要很了解館的發展歷史;同時,一座博物館要能運作下去,也必須對館藏和歷史,不斷的盤點、分類和整理。」無論此時史博館的行動和創造,看來如何新穎,說到底都是持續的自我挖掘罷了,「光是這兩年多下來,我就發現它是個大寶庫。」
博物館的本職所在,從來都是以現在的方式、看過去,然後帶領大眾走向未來。於是,依循著這樣的路徑,所有的新與轉化,本質都立基於舊有的事宜;而一切關乎博物館、乃至於人類的未來取向,也得更仰賴典藏過去。所以明白了策展、運營、推廣或轉型,該做的都是同一件可長可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