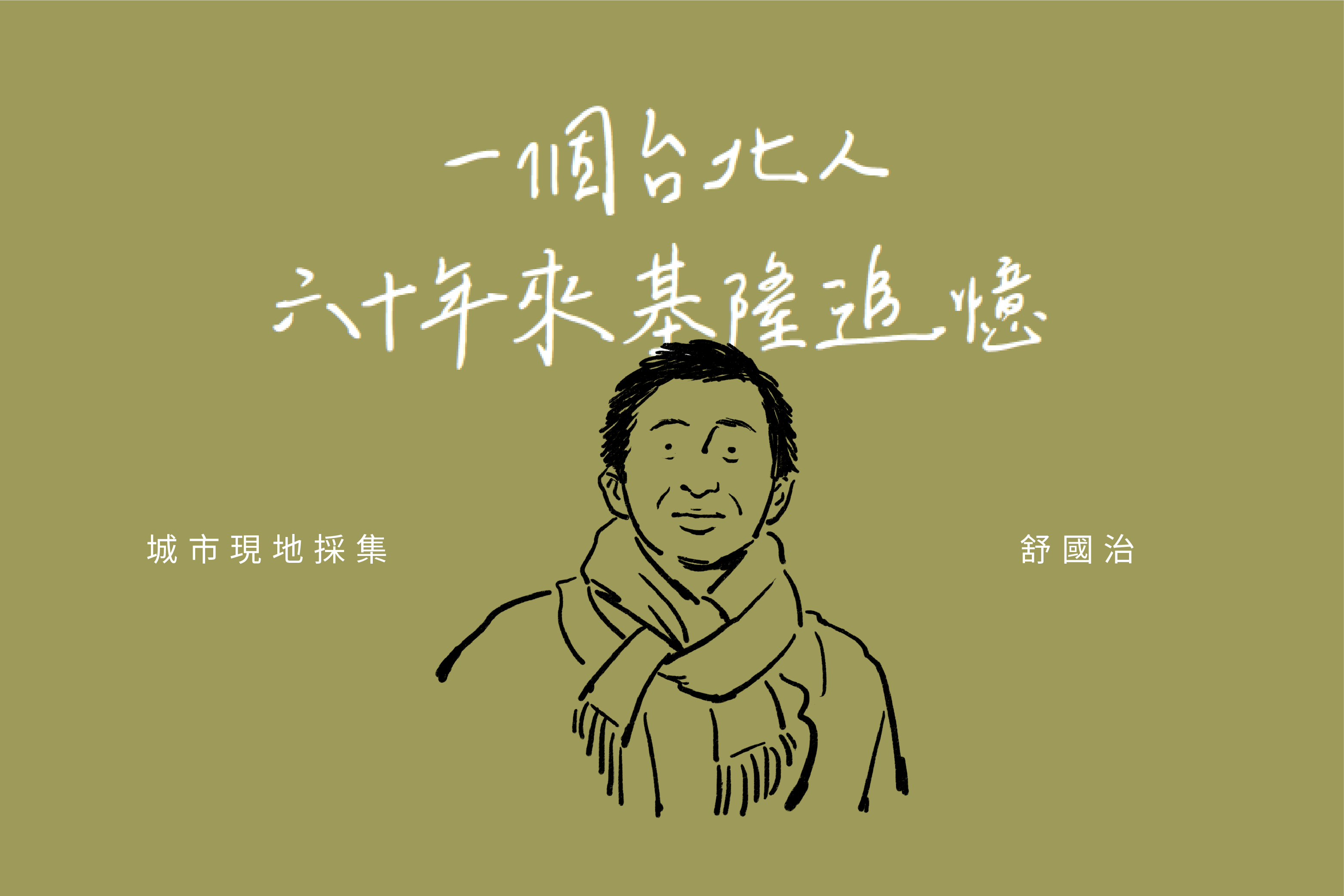專題:在基隆:城、海、山與未來
舒國治:一個台北人六十年來基隆追憶
六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的海,是在基隆。而且,不是看海灘,是看到海港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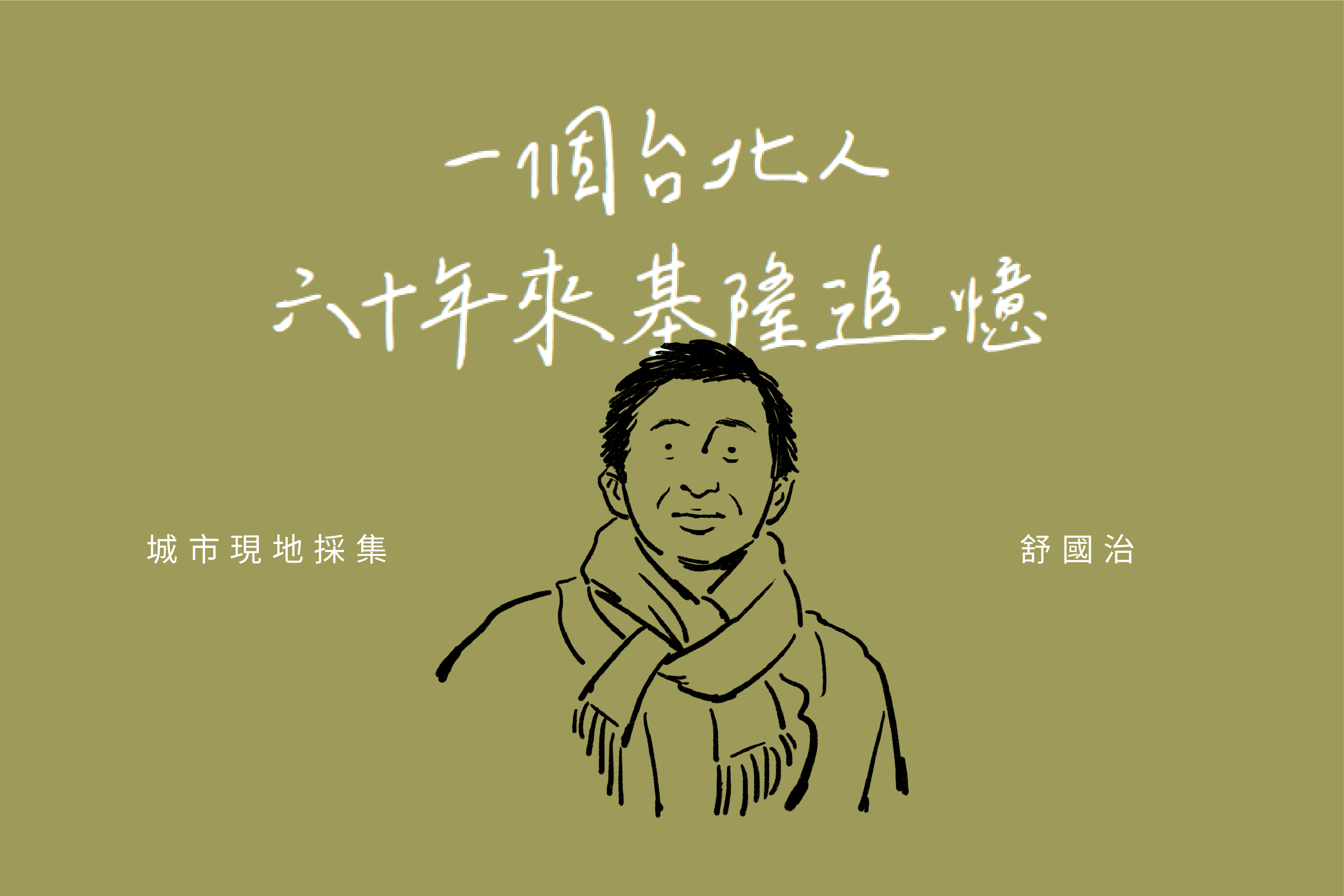
我很常跟朋友說,基隆,是全台灣我最喜歡寫、最喜歡談到的一個城市。
為什麼?我也不確定。但我東想西想,一定是某種在我童年就深深烙印在眼界裡腦海裡的幽幽微微景致、氣息、氛圍吧。
於是你就知道,城市是有一種氣氛的。城市也是有一種異鄉感的。這方面,五、六十年前的基隆,它在台灣是很出眾的。可以說,基隆太特異了。
六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的海,是在基隆。而且,不是看海灘,是看到海港的海。
那時候我媽,偶爾會去基隆看望同鄉,有時還坐下打幾圈麻將什麼的。四十年代末,無數的外省人在此下船。基隆,是他們在台灣認識的第一個城市。二十多歲時,在七十年代,我聽一個祖籍山東的朋友說,他們家在基隆住了十多年才搬到台北,原來他爺爺為了將來(所謂「不久的將來」)從台灣回返故園,自基隆等船登船等可以排得比較前頭。正是這樣的考量,有的家庭索性安家在基隆,而不住那些離港口遠、離大船遠的台北啦、台中啦等城市。
我跟著媽媽下了公路局(乘火車較少),通常會乘三輪車去朋友家,會沿著「田寮河」而行。只見河上浮著密密麻麻的猶未去皮的大木頭,有當地小孩在上面踩著走著,如同是走在彈簧上那樣來玩。我看著感到有趣,卻馬上被誡,說前兩天才有小孩一踩把兩根靠攏的原木踩分開,人掉了下去,隨即兩木合攏,小孩從此再沒有上來。
這一條河,大家現在叫田寮河,早先,也被叫做「博愛河」。但我做小孩子時,只叫他「運河」。河上每隔不遠,有小橋,有的還微呈拱形,老實說,真是很美。下雨時(基隆那時雨極多,一年中超過二百天),人們打著傘,低著頭匆匆過橋,簡直像極了日本劍道片的那種淒涼卻又有韻。
我和我的同輩小孩,在五十年代(即二十世紀的中段)初出生的,我們所處的周遭,日本感是很濃重的。房子的模樣、街道的格局、色澤的偏黑等等。而基隆的這種日本感,更因多加了山坡與大海,顯得更是陰鬱。如果小孩當年看了日本片像《赤胴鈴之助》、《里見八犬傳》、《黃金孔雀城》之類,晚上走在基隆的河邊、橋上、或是山坡巷弄,那也真太鬼氣森森的日本感啊!
這個我台北以外第一個遇見的城市,其實在景致上我寓目得更有豐富之感。主要那時放眼可以看得很全面。山在哪裡,海在哪裡,山坡上的房子(如延平巷)又是何等形樣,運河又在哪兒平躺著,橋又跨在哪兒⋯⋯全是那麼布展得極為妥宜,又全在人的眼角不遠處。
除了東面的田寮河,當年西北面流來的西定河,到了城市南緣,向北流,夾在孝一路與愛一路之間,這條河叫「明德河」,也是城市的美景(就像京都有些白川的小段落或高瀨川的小段落),如今也早已看不到矣。
二十年代,人要去大陸,也須在基隆上船,再航至上海等。以昔年台灣最有學問的彰化仕紳洪棄生(1866~1928)為例,一九二二年他帶兒子洪炎秋赴北京讀大學,從中部乘火車先抵基隆,彼時未必有像樣旅館下榻,而他又是仕紳,於是得以住在另一個仕紳的家裡,便是顏家的「陋園」。
十多年前,我也曾在「陋園」外眺看了幾眼,深感當年基隆房舍不多、建設鮮少的那股清美,確實很該教基隆人自豪。
基隆,一直是個現代化城市。哪怕基隆人的空間崎嶇、基隆人的過日子未必比苗栗公館或南投竹山安詳舒泰,然公館、竹山不是現代化城市。基隆人的態勢,就透顯出一股城市氣。這在三、五十年前即已如此。
基隆的城市設施,在公車上最早即顯出它的現代化。與中南部的城市之難以公車普及化,相當的不同。
說到公車路線,像 1 路,人人馬上說「到和平島」。一說 2 路,馬上說「到市立三中」。一說 5 路,會說「到八斗子的」。
那些念「基水」或「海洋學院」的,最熟悉的祥豐街,會說「公車要坐 1 甲」。
那些在台北沒考上分數高的學子,有的高中唸了「基水」(基隆水產),則必須一早乘火車通學。聽他們坐火車上學的故事,不管是「淡水線」的,或是萬華的、新店的「萬新鐵路」,或是「基隆線」的,車廂內的打架、或談戀愛故事,都是我們在市內不曾火車通學的孩子很羨慕的經歷。尤其「萬新線」(即今日的汀州路)會經過的強恕中學,會經過五峰中學,會最後抵文山中學,這一路的「武林高手」特別多,故打架的故事特別精彩。
「基隆線」因有「基水」,也是「武功不弱」的學校,故車上也充滿刺激故事。
有時在台北上車,沒有雨,但基隆說不準,於是學子愛拉風,會穿上風衣,若在基隆遇雨,猶能稍擋。這是六十年代,亞蘭德倫穿的也是風衣。
其實學子那麼小就搭火車往遠處上學,是很能在小小心靈中種下「遙遠」或「天涯海角」的人生視野。侯孝賢拍的《戀戀風塵》,就能呈現那種少年人的對未來的迷茫。
基水畢業的人才,我恰好認識兩個,一個是在金馬獎常得大獎的攝影大師李屏賓,一個是自八十年代起就名聞畫壇的畫家鄭在東。
基隆是這麼的有滋有味,我不只一次和鄭在東、李屏賓聊到,怎麼沒有一部描繪到基隆的電影呢?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與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用到金瓜石、九份做場景,其實是對基隆這個雨都的延伸。
基隆的山海,夾得極緊,令基隆的胸腹之地很是拘窄;於是基隆的製吃,往往能在小小方寸之間把食物弄得小中帶巧。這在至少這五、六十年裡各街巷騎樓間設鋪子擺攤子的店家常有香美卻又簡淨的飯菜可以見出。
不只是廟口的小吃而已。
十五年前,我在「商業週刊」專欄提到的廟口 19 號晚上(白天是「光復肉羹」)的「何家滷肉飯」,被我稱「全台最好」,如今固然早已收掉,成為絕響。但當年這位何鐘福老先生,他製吃之手法,可見出在「小」與「簡」之中的巧思。他的豬肉料理,赤肉、腿肉、豬腳都燙燒完淨,斬成恰好大小,鋪陳在案板上,等著隨時入湯。那種白燒之法,十分「現代」,十分「城市」,簡直能在東京和眾店家並列。同時非常符合基隆這個「現代港口」的城市風味。
廟口小吃,何等的大名氣;但我平生吃的第一碗日式豬排飯(Katzu Don),是在基隆廟口的那家當年應算高級的日本料理店「神州」。那是一間日本房子,那碗丼,當然是裝在有蓋的漆器碗裡,六十年代中。
「神州」也不在很多年矣。問五十歲以上的基隆人,當不至陌生。倘問七、八十歲以上的基隆人,或許講起「神州」,還勾出了極多的舊日基隆繁華。
老年代的基隆食景,是各街各騎樓皆有美味,並不只有廟口而已。如今廟口熱熱火火的紅了太多年,近十年據說也不是攤攤皆能維持著昔年水平。於是會吃的老饕,除了在城區內找早期質樸的料理,也會到暖暖、到猴硐、到瑞芳找逐漸在基隆消失的老年代口味,是一樣的道理。
依山面海,住得極緊,所以六十年代初我在基隆看一部電懋公司出品的黑白電影《寶蓮燈》,是在有三層樓座位的「中央戲院」(在仁三路),你看看,三層,往下望去,很陡。
這是基隆市。向西一些,離海更遠的七堵,則腹地也比較平曠了。這裡的生活,或說老百姓的情態,就也比較平曠了。不像基隆人的凝重,收緊。
六十年代我唸初中,班上就有兩個七堵同學,每天坐火車通學。而他們,不選基隆的學校念。
六十年代,我作為一個少年,凡是去海邊,指的便是基隆。後來野柳流行了,金山流行了,那對我而言,皆是基隆這個海港的延伸。
有一次,我也去了八斗子。那天在沙灘上打赤腳走著,一不小心踩到了蚵仔的尖殼,血流如注,便這麼顛著簸著回到了台北。
基隆的地形,相當打造成它的格調。在層層疊疊的群山之後,有小溪流下;流向海的這面的,就只能是短而小的,於是造就了基隆這個小凹凹槽的美麗港口,然胸腹太緊了。至於從雙溪鄉群山流出的小溪,流往台北方向的,則蜿蜿蜒蜒的流成了大河,便是經過瑞芳、暖暖、汐止等地最後到了台北的基隆河!
這形成了在幾十年、甚至近百年的落腳過程中有流行所謂這麼一句話:「基隆人打拚最後,都希望搬進台北去。」這就像說瑞芳人、暖暖人都期望一日搬到基隆去,是類似的說法。
噫,其實基隆是何等挺拔多姿,哪裡要跟那些平白無奇的大而空曠之域一較優劣呢?
經過了六十年,我真希望我童年、少年時的基隆那舉世無雙的絕代風華,還能在哪裡看到嗎!
舒國治|台灣作家、美食家。早年從事電影工作,之後轉而投入寫作,作品以散文、遊記、短篇小說為主。曾獲得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有《門外漢的京都》、《台北小吃札記》、《宜蘭一瞥》等。
回到專題:在基隆:城、海、山與未來